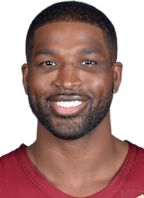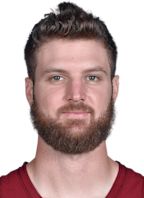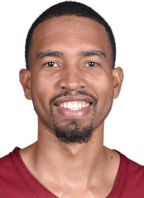搜尋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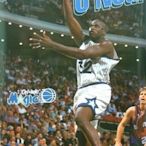 $300NBA克里夫蘭騎士歐尼爾O`Neal早期魔術隊原版海報Y3606323407
$300NBA克里夫蘭騎士歐尼爾O`Neal早期魔術隊原版海報Y360632340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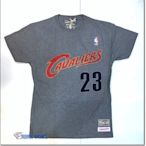 $1100*dodo_NBA 進口m&n Lebron James 姆斯 小皇帝 LBJ 新人年克里夫蘭騎士 棉短T T恤dodo-暫時關閉賣場中
$1100*dodo_NBA 進口m&n Lebron James 姆斯 小皇帝 LBJ 新人年克里夫蘭騎士 棉短T T恤dodo-暫時關閉賣場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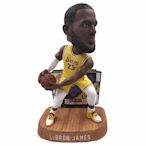 $1900克里夫蘭 騎士 Anthony davis lebron james 洛杉磯 湖人 lakersY1491318241
$1900克里夫蘭 騎士 Anthony davis lebron james 洛杉磯 湖人 lakersY1491318241 $1680【ANGEL NEW ERA】NEW ERA NBA 克里夫蘭 騎士 大C 復古LOGO 經典黑 59FIFTY 棒球帽ANGEL NEW ERA
$1680【ANGEL NEW ERA】NEW ERA NBA 克里夫蘭 騎士 大C 復古LOGO 經典黑 59FIFTY 棒球帽ANGEL NEW ERA![全新真品附吊牌 Adidas Swingman 克里夫蘭騎士復古 Daugherty 黃金M號 全新真品附吊牌 Adidas Swingman 克里夫蘭騎士復古 Daugherty 黃金M號]() $3280全新真品附吊牌 Adidas Swingman 克里夫蘭騎士復古 Daugherty 黃金M號Y7608549088
$3280全新真品附吊牌 Adidas Swingman 克里夫蘭騎士復古 Daugherty 黃金M號Y7608549088![【ANGEL NEW ERA】Mitchell&Ness M&N 克里夫蘭 騎士 酒紅 帽 可調帽 SNAPBACK 【ANGEL NEW ERA】Mitchell&Ness M&N 克里夫蘭 騎士 酒紅 帽 可調帽 SNAPBACK]() $1180【ANGEL NEW ERA】Mitchell&Ness M&N 克里夫蘭 騎士 酒紅 帽 可調帽 SNAPBACKANGEL NEW ERA
$1180【ANGEL NEW ERA】Mitchell&Ness M&N 克里夫蘭 騎士 酒紅 帽 可調帽 SNAPBACKANGEL NEW ERA![全新NBA克里夫蘭騎士Cleveland Cavaliers斜袖七分袖SZ M台中可面交 全新NBA克里夫蘭騎士Cleveland Cavaliers斜袖七分袖SZ M台中可面交]() $700全新NBA克里夫蘭騎士Cleveland Cavaliers斜袖七分袖SZ M台中可面交非潮流 低調享受
$700全新NBA克里夫蘭騎士Cleveland Cavaliers斜袖七分袖SZ M台中可面交非潮流 低調享受![2022-23 Panini Noir 黑國寶 克里夫蘭騎士 主力Evan Mobley 限量49張🔥 球隊Logo 質感美卡 2022-23 Panini Noir 黑國寶 克里夫蘭騎士 主力Evan Mobley 限量49張🔥 球隊Logo 質感美卡]() $3492022-23 Panini Noir 黑國寶 克里夫蘭騎士 主力Evan Mobley 限量49張🔥 球隊Logo 質感美卡棄標一律黑單+負評
$3492022-23 Panini Noir 黑國寶 克里夫蘭騎士 主力Evan Mobley 限量49張🔥 球隊Logo 質感美卡棄標一律黑單+負評![【ANGEL NEW ERA】Mitchell&Ness M&N NBA 克里夫蘭 騎士 酒紅色 復古LOGO 老帽 【ANGEL NEW ERA】Mitchell&Ness M&N NBA 克里夫蘭 騎士 酒紅色 復古LOGO 老帽]() $1280【ANGEL NEW ERA】Mitchell&Ness M&N NBA 克里夫蘭 騎士 酒紅色 復古LOGO 老帽ANGEL NEW ERA
$1280【ANGEL NEW ERA】Mitchell&Ness M&N NBA 克里夫蘭 騎士 酒紅色 復古LOGO 老帽ANGEL NEW ERA![全新NBA克里夫蘭騎士Cleveland Cavaliers logo短T SZ M台中可面交 全新NBA克里夫蘭騎士Cleveland Cavaliers logo短T SZ M台中可面交]() $800全新NBA克里夫蘭騎士Cleveland Cavaliers logo短T SZ M台中可面交非潮流 低調享受
$800全新NBA克里夫蘭騎士Cleveland Cavaliers logo短T SZ M台中可面交非潮流 低調享受![【豬豬老闆】NEW ERA 9FORTY 950 海軍藍 紅 克里夫蘭 騎士 棒球帽 帽子 童 NE70381069 【豬豬老闆】NEW ERA 9FORTY 950 海軍藍 紅 克里夫蘭 騎士 棒球帽 帽子 童 NE70381069]() $880【豬豬老闆】NEW ERA 9FORTY 950 海軍藍 紅 克里夫蘭 騎士 棒球帽 帽子 童 NE70381069★★豬豬老闆 美國代購★★
$880【豬豬老闆】NEW ERA 9FORTY 950 海軍藍 紅 克里夫蘭 騎士 棒球帽 帽子 童 NE70381069★★豬豬老闆 美國代購★★![全新 Bearbrick 400% NBA Cavs Cleveland 克里夫蘭騎士 全新 Bearbrick 400% NBA Cavs Cleveland 克里夫蘭騎士]() $12800全新 Bearbrick 400% NBA Cavs Cleveland 克里夫蘭騎士Oh Yeah !! 鼠PP
$12800全新 Bearbrick 400% NBA Cavs Cleveland 克里夫蘭騎士Oh Yeah !! 鼠PP
2024年4月17日 · 那紙差點成真的古巴飛彈危機「開戰布告」:關於甘迺迪講稿捉刀者的奧祕. 1962年10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對國民發表演說,宣布從10月24日開始對古巴進行封鎖。. (攝影/AP Photo/Bill Allen). 俄侵烏戰爭裡,普丁不放棄以核武作為要脅。. 回望61年前的古巴危機 ...
- 利用一戰後德國人的屈辱不平壯大自己聲勢
- 「靠口才打動群眾」,希特勒與納粹黨打壓異己、藉民選崛起
- 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上的心力遠比政策內容要多
- 21世紀獨裁者的統治利器:媒體與沒有選擇的「選舉」
- 用秩序、和平口號「合理化」野心
- 追隨者的盲目崇拜,是獨裁統治推手
戰勝的協約國1919年強迫德國接受嚴苛的和平條件,再加上192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率,以及之後的嚴重失業問題,都讓希特勒1919年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在1920年代得到立足之地,但20年代下半經濟得到某程度復甦後,他們仍然只是一個邊緣政黨。這種局面在1929年10月華爾街崩盤後改變。這個衝擊使得德國銀行收回給企業的貸款,到了1932年每3個工人就有1個以上失業。希特勒的政黨是這場經濟危機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在1928年的國會選舉拿下12席和2.6%的選票。1930年9月的國會選舉更增加到107席次,得票率18.3%。納粹黨一躍成為議會第二大黨,超過6百萬人投票給它。 希特勒的主要立傳人伊恩.克索(Ian Kershaw)提出了一個概括性解釋,不只適用於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有些時候,政治...
希特勒心裡卻有別的盤算。1933年2月27日國會大廈被燒毀更幫了他大忙。 這件事是意外,是荷蘭某個社會主義青年的個人行動,希望藉此刺激德國工人挺身反抗右翼政府和資本主義。希特勒卻趁機把縱火案怪在共產黨身上,並開始打壓共產黨員,連社民黨員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也遭殃。 1933年3月5日,在充斥著恐嚇的選舉中,納粹黨拿下將近44%的選票,新國會的647席有288席被他們拿走。共產黨雖然被殘酷打壓,許多共產黨員和社民黨員被打甚至被殺,但共產黨的得票率仍逾12%,社民黨也有18%。然而,這時納粹不只成了第一大黨,也因為跟保守派結盟而成為國會多數黨。事實上,他們甚至不需要依賴後者的支持就能掌權,因為納粹讓當選的共產黨議員都無法就職,這些人不是被捕就是逃跑。國會在衝鋒隊(SA)和親衛隊(SS)這兩個組織的...
1934年時,一般人提到希特勒都稱「我的元首」,而他自己在跟大多數納粹領袖人物說話時都直呼他們的姓。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雖然當時還沒有出現「形象」這樣的字眼)上的心力遠比政策內容要多,只有他深深著迷的領域例外,例如消滅猶太人的影響力(最後變成消滅猶太人本身)、增強德國的軍事力量,以及外交政策。 納粹體制有一個重要的層面不能算極權體制,那就是其他許多政策的辯論都在希特勒之下的層級發生,下級會遵循他的大方針,做事盡可能合他的意。這樣反而增強了他的無限權威,雖然難以親近、無法預測的任意干預、冗長的獨白和對政策細節缺乏興趣的領導方式,很難造就有效率的政府。 希特勒討厭可能會出現批判性討論的內閣會議。1933年他還帶領著聯合政府,裡頭的保守派多於納粹黨,內閣一個月開4、5次會,直到夏季休會,但之後次數...
專制統治確實遲早會刺激受害者站起來推翻政權(雖然暴力革命往往是另一種威權統治的序幕)。然而,即使是獨裁君主也無法只靠武力統治,因為他必須要能說服周圍的人(他的禁衛隊、軍隊將領或政治警察頭子),讓他們相信效忠他有利於國家或個人利益(更常是兩者都有)。 比杜爾哥年長一些的大衛.休謨(David Hum)認為,「要是一個暴君的權威完全來自恐嚇,就沒有任何理由要害怕激怒他。因為他身體的力量能影響的範圍很小,他進一步擁有的力量一定要奠基在我們自己的想法,或是其他人認定的想法上。」 因此,說服力和武力都是獨裁領袖不可或缺的裝甲。20、21世紀的獨裁統治者擁有啟蒙時代思想家想像不到的利器和媒體,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發揮極致的大規模群眾集會,到電子監控、廣播電視,甚至對傳送訊息的完全掌控。左右民意需要組織的幫...
極權政權為了合理化執政黨和領袖對徹底掌權的野心,通常會描繪出一幅輝煌的前景,一個新的黃金時代,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鼓舞大批人民,蘇聯、義大利和德國就是如此。用來合理化極權和威權統治另一種較為普通的論點是,這樣能重建秩序,穩定政府。秩序之說很吸引人,因為一般人多數時候都希望有和平的環境,在穩定的社會中養兒育女。倘若有人告訴他們,不選擇獨裁政權承諾的「秩序」,就是選擇內戰和無政府狀態,而他們也相信,很多都會樂意或勉強支持當權者。 然而,這樣把「秩序」合理化有幾個根本的問題。 首先,大多數威權政權本身就不顧法治,訴諸暴力並拆散家庭,動輒逮捕、拘禁、殺害好幾萬人(如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甚至數百萬人民(如史達林統治的蘇聯或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造成大規模混亂。無論怎麼定義「秩序」,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
眼光遠大的偉大領袖,就是獨裁政權最難以動搖的迷思。這在專制政權比寡頭政權明顯,後者通常把重點放在執政黨的獨特洞察力和智慧上,而非個別領袖的特質。義大利文(Duce)、德文(Führer)和俄文(vozhd)的領袖所代表的意義,在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史達林執政時都產生改變。每一個都代表一個力量、理解力、洞察力超乎常人,而且愛民如子的領導人。 盲目的追隨者賦予領袖英雄特質,有時領袖本身甚至尚未標榜自己擁有這些特質。最顯著的例子是希特勒。他先是相信德國需要一個偉大英勇的領袖,後來沾沾自喜地發現自己就是那一個人。1920年代早期,希特勒還沒開始打造個人崇拜(有別於當時的墨索里尼),但追隨者卻已經聲稱他們「找到了數百萬人心的渴望──一個領袖人物」。到了1920年代末,希特勒相信他們是對的,納粹黨也開始完...
2024年4月4日 · 本文為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蕭育和為《鐵幕降臨》撰寫的推薦序,經衛城出版授權刊登,文內小標為《報導者》編輯所添。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 鐵幕東歐的共產體制,更著力於對公民社會的滲透與掌控. 確實,最起碼從1946年起,直到1989年曙光初露,東歐在民主化之前經歷將近50年的共產統治,不算另一個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小國的話,堪稱全球最長的戒嚴(編按) 。 蘇聯在鐵幕東歐所打造的體制,即便方方面面依據「極權」原則打造,確實也並非典型的極權體制。 它們的存在是共產全球革命的先鋒堡壘,卻不負責輸出革命的任務,整個體制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對內穩定小史達林們的專政,對外抵禦西方集團以及「狄托分子」的滲透,儘管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美國在甘迺迪執政之前對於東歐有任何系統性的著力。
2024年4月15日 · 本文介紹3部頗具代表性的新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導演豐沛的創造力和深刻的反省能力,讓人在這個飽受戰爭摧殘的國家看到不滅的希望。 有別於其他國際影展,柏林影展選片強烈呈現多元價值、讓議題彼此對話的特色,對於世界正在發生的「大事」,更是柏林影展年年關注的焦點。 過去兩年,許多烏克蘭影像作品透過柏林影展首度面向世界,從導演的鏡頭讓人們第一手、更細緻地認識戰火下的烏克蘭。 Ⅰ.現實遠比虛構殘酷──開戰後回看《編輯部》 《編輯部》導演波達修克(Roman Bondarchuk)是年輕世代電影人的佼佼者,在烏克蘭享有盛名。 (攝影/林育立) 今年柏林影展最受期待的烏克蘭電影,首先是波達修克(Roman Bondarchuk)執導的 《編輯部》(The Editorial Office) 。
2022年3月30日 · 位於烏克蘭哈爾基夫市附近的大屠殺紀念館(Holocaust Memorial in Drobitsky Yar),紀念碑狀似燭台,是為了緬懷在二戰納粹大屠殺中遇難的猶太人,2022年3月26日遭俄軍空襲破壞。 烏克蘭國防部在Twitter寫著:「納粹已經回來了。 整整80年後。 」(攝影/AFP/Sergey BOBOK) 【精選書摘】 本文為 《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 導讀,經衛城出版授權刊登,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2023年2月23日 · 波蘭作家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在2023年初來台,於台北國際書展波蘭主題館舉行《克林姆林宮的餐桌》新書講座。 (攝影/陳曉威) 冷戰時期,只有真的戰鬥不能碰以外,資訊戰要鬥、上太空要鬥、增加軍備要鬥、經濟和生產力要鬥、盟友更加要鬥,其中一項要鬥的還包括飲食。 維特多在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新鮮出爐譯好繁體中文版的 《克里姆林宮的餐桌》 裡,再次展開描寫了食物與權力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上一本書 《獨裁者的廚師》 中,他已經寫過蘇聯廚師對於權力的控制慾。 一名跟隨伊拉克獨裁者海珊的廚師說:蘇聯連廚師都表現得像超級大國一樣,我們在一間巨大的廚房裡備膳,裡頭用的是瓦斯爐,而他們每隔一會兒就會挪一下我們的鍋子。
2019年4月16日 · 斯維特里娜・扎里希查克(Svitlana Zalishchuk) 是廣場革命後晉身議會的年輕代議士之一。 革命前已投身民主運動的她,2014年與另外數名革命領袖加入現任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的名單,當選國會議員。 從立法者的角度看,烏克蘭這5年來的變化是明顯的。 波洛申科政府執政初期,乘著支持變革的民氣高昂,快速推行了多項改革,包括成立獨立的國家反貪局、強制公職人員申報資產、建立開放的政治招標系統等。 2004年,烏克蘭爆發過橘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 ,雖然後來演變成親歐派的權鬥,但確實放寛了社會的政治氣氛,讓公民社會能夠發展起來,孕育一批具政治、社會參與經驗的年輕人。